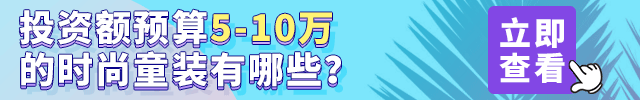空中天使:拼妈的节奏
- 2020-12-17 07:43 童装加盟网
在当今,教育“拼妈”已成为中国都市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。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,一方面表现为孩子的受教育年龄不断提前,另一方面是家长对教育的高度介入。而这种介入往往是由妈妈们身先士卒、全力比拼的。她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“陪读”、课程辅导、搜集各种教育信息以及和学校老师保持良好互动之上。甚至有观点认为,一个家庭的教育成功与否,很大程度是由妈妈们的比拼程度决定。
那么,这一现象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效应?形成教育“拼妈”这一表象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?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?

1、教育的母职化与父亲缺席
教育要“拼妈”,那爸爸去哪儿了?当教育“拼妈”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,也就意味着父亲在孩子教育之中的“缺席”。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,有职业的母亲中52.5%的人承担了辅导孩子功课的“大部分”或“全部”工作,而男性所占比例仅为16.4%。可见,父亲的教育参与度明显偏低。实证研究显示,父亲也不是全然不参与,但都是间断性或“一时兴起”式的。然而,父亲缺席也并不表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不关心、不介入,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候出马,比如择校、买学区房、升学填报志愿时。
当教育变成一种家庭投资行为之后,我们看到家庭内部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——大多数父亲处于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地位,而把需要耗时费力的教育介入和课业管理工作统统交给了母亲。
对于为什么多数父亲会缺席教育,最普遍也是最“合理”的解释就是:男人忙于事业,要挣钱养家,因而无暇顾及。这种性别分工规则,是建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:在职场上,男性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晋升前景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指出:“妇女的时间价值可能是较低的。”
但他却没有指出另一点,如果说女性时间价值较低是一个严酷的事实的话,那也是职场存在性别歧视所致。
教育的母职化和父亲的教育缺席,看上去是夫妻间基于经济理性的分工,但实际上却导致了教育的失衡。
2、教育“拼妈”导致教育焦虑症蔓延
由教育引发的焦虑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。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,92.8%的受访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心理。“教育焦虑症”主要发生在母亲身上,“妈妈们是此症高发人群”。家长类网上社区是妈妈们彼此交换教育信息、获得相互支持的重要阵地,但也是焦虑情绪相互感染并放大的场域。
有文章称,不应把“拼妈族”的教育焦虑归结为“社会焦虑”。理由是国外的全职妈妈比中国多,她们在对孩子的付出上一点都不少于中国的“拼妈族”,怎么就没听到她们的抱怨呢?因此,该文认为这些妈妈的焦虑源自好“攀比”和“炫耀”等个人问题。
教育焦虑症到底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?是什么使她们变得如此“疯狂”?
首先,教育焦虑来自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紧张。而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为教育市场所操纵——市场本身需要制造需求和因匮缺造成的焦虑。从不断遭到质疑但又影响力巨大的“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这样的口号,到不断翻新的家教新概念,从制造哈佛女孩的“成功母亲”的现身说法,到“教育专家的忠告”。这一切在引发母亲焦虑的同时,又仿佛在给出解答——教育市场能为你提供各种解决良方,只要你愿意为此付费。
其次,应该看到个体的教育焦虑也是由文化重构的“好母亲”标准所致。今天,一个母亲如果只能在生活上对子女尽养育之责是不能算优秀的,“母不在于慈而在于教”。而“拼妈”比拼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,还包括她们的“教育理念和自身的综合软实力”。网络上认为理想的妈妈要十八个“得了”——“下得了菜场,上得了课堂……教得了奥数,讲得了语法,改得了作文,懂得了琴棋,会得了书画……” 可以说,跟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媒体所塑造的“超级妈妈”相比,这一“全能妈妈”的理想化标准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而,几乎所有的妈妈在此标准前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。
3、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“拼妈”现象
有文章认为:“相对于‘拼爹’而言,‘拼妈’应当算是一种进步。‘拼爹’拼的是父辈的权势和财富,破坏了社会公平、阻碍了阶层流动,所以遭人诟病。而‘拼妈’则是一种个人竞争,且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。”引用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妈妈的话:“拼钱、拼权、拼地位、拼关系,我拼不了,唯一可拼的是辅导孩子学习。”似乎教育“拼妈”拼的是妈妈的时间和精力,这要比拼权和钱公平得多。美中不足的是,妈妈们之间的过度比拼导致了教育焦虑等问题的出现。
但不得不指出的是,“拼妈”的背后还是“拼爹”。妈妈们拼的似乎只是个人的精力和能力,其实最终还是要比拼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本,包括经济资本、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。即便仅仅是比拼实力,也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持。无论是购买学区房还是孩子上“补习班”,都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。而低收入劳动者在经济资本、文化资本方面都毫无优势,几乎不得不放弃加入这场竞争。
“家长主义”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,以个体选择自由、家长自主择校、介入教育、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说辞,把教育变成一项比较家庭投资的体系。当然,最终个人教育的成败要由“投资者”——家长的选择偏好和介入能力决定。这一教育转向使拥有较多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中等收入群体获益,而不利于底层家庭。因此有学者认为,“家长主义”使教育成为了一种事业,它更多地依托于家长的财富和意愿,而非学生的能力。这与强调机会均等的“能力主义”相悖,也和教育的公平性相悖。
“家长主义”之所以能在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以及欧美不少国家成为主流,是因为它正好同时吻合了保守主义以及自由市场双方的意向,成为当时社会不公平的替罪羊。它在“自由选择”、“家长权力”的名义下,将教育的不平等合理化,将教育与社会等级化的责任,推给个人与家庭。同时,它也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相关。如今,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方式已经变化,社会阶层的传承已不再完全依靠原有经济财富的传递,在这种情况下,中等收入群体需依靠“文凭竞争”来确保其再生产的社会优势,而有能力的家长则为孩子购买有竞争力的优势。由此,教育不再与社会“公平”与“公正”相关。
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,“家长主义”迹象在中国也有所显现。尽管教育部门一向坚持“促进义务教育向公平、公正、均衡的目标发展”的非市场化原则,但当义务教育体系外滋生出庞大的“隐形市场”、教育变成“隐形市场”下的竞争时,市场原则已成为教育场域中强有力的行动逻辑,这不仅会侵蚀公共教育,还会强烈冲击到教育的公平性。